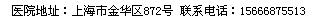您的当前位置:上消化道出血 > 疾病危害 > 医院主任医生的灵魂拷问永不放弃的治疗
医院主任医生的灵魂拷问永不放弃的治疗
北京皮肤科哪里医院好 https://m-mip.39.net/nk/mipso_4658077.html来源:格致论道讲坛(ID:SELFtalks)作者:宁晓红面对死亡我可以做什么?“我们面对重病,面对临终,我们有选择。我们可以找人帮忙,可以表达自己的意愿,按照自己的方式离世。”医院老年医学科主任医师朋友们,大家好,我叫宁晓红,医院的一名医生。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的内容是善终离我们有多远?当我要谈“善终”这个话题的时候,我不知道各位有什么感受?你是不是会觉得有些害怕呢?会不会不想听这个话题?宁大夫她会讲什么呢?我不想听这个话题,来点儿起死回生的吧,像北京东单路口救人的那种:性命危在旦夕,医生实施紧急抢救之后就能挽回生命。大家不要害怕,今天的内容一定会让你有收获,而且带着温度。医生的“痛苦”首先我跟大家介绍我自己:我是从年开始做医生的,已经做了23年,也算一个中年医生。我做医生的过程不容易,经历了很多痛苦。这个痛苦是什么?不是说值夜班,不是说加班,不是说身体的累,是我遇到了很多我不能面对的问题。我常会问我自己:作为一名医生,我能怎么办?我能做一个好医生吗?在我年轻的时候,就是前一两年做住院医生的时候,我就遇到过这样一个病人:20多岁得了淋巴瘤,经过很多程的治疗,他已经不能再治疗了,生命走到了终点。那一天我值班,他就要死了,那他的表现是什么呢?就是呼吸困难,喘不过气,我们需要给他加氧气。当病人面临死亡,就需要高年资的医生来诊断。当时我是最年轻的,我的任务就是扶着他的氧气面罩,所以当时我看到他每喘一口气一呼气,喷到氧气面罩上很多小小的血点。当时的我没有感觉,我觉得我是麻木了,我并不害怕,也没有其他的感觉。我就扶着那个面罩一直到他死去。我没有跟他说过话,也不知道他家人在哪里,他们是什么感受。但是这么多年走过来我回头望当时的自己,我觉得我做的很不好。当时我年轻,但这不是理由,我觉得我应该在那个时刻做的更好一些。后来在我完成了六年的内科轮转,进入我的第一个专科:肿瘤内科。我在肿瘤内科工作了十二年,在这十二年间,我觉得我受到的煎熬是很大的,虽然也有成就感。我们给病人做治疗,让他们延续寿命,甚至有一些是术后化疗,他们治愈了。但是让我印象深刻的不是这些,是那些我无能为力的事情。病人和家属很相信我。当他们问我这样一个问题的时候,我会感到无能为力,这个问题就是:“宁大夫,现在真的没有方案了吗?”因为大家知道打化疗是一个方案接一个方案,可能我先开始用一个方案,没有效果换第二个,再没有效果就换第三个。我还有多少个方案可以换的呢?其实没有那么多。所以,那时候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回答他们。其实,我该跟他们说:“真的没有方案了”,可是我却感觉说不出口。因为我认为这并不是他们想听到的,所以我会说“没问题,你稍等等,我们再研究研究,过几天就有方案了”。其实这并不是真的。所以在那个时候,我非常非常难过,因为我帮不了他们。而这种难过,我没法跟任何人表达,这种无助的感觉,侵蚀着我的内心。大家也听说过,医生这个职业耗竭感特别明显。其实,不光是我在经历过这些痛苦,我的同事们也经历过,或者正在经历。前不久,有一个年轻的、工作仅两年的住院医生跟我们分享了一件事情。他说:“今天我抢救了一个42岁的年轻女性,她是肿瘤晚期。家属早就表明态度,哪怕她到了晚期也是要抢救的,哪怕让她多活一秒。”所以当她呼吸突然没有的时候,医生们就给她进行了抢救。按压、电击、插管,最后她心跳恢复了,但是却没有神志,不能交流,只能躺在那儿。然而,当家人看到她情况以后,说:“怎么变成这个样子了。这太痛苦了,我没有想到是这么痛苦,我们不希望她这么痛苦的离世,这些仪器请帮我们都拿下来。”当把这些仪器拿下来的时候,病人就开始抽搐。年轻的住院医生束手无策站在那儿,不知道怎么办。病人就这样一直抽搐了几个小时,最后离世了。年轻的医生说:“今天我真的受到了严重的心理创伤。”在这样的时刻,医生真的很无助,这就是我们经历的痛苦。很多时候,尤其面对死亡的时候,作为医生,我们会感到无力、无助、悲伤。我特别希望有一个方法,能够帮助我们来面对这些痛苦,所以在这过程中,我就不断地去学习。在学习过程中,我读到了一本书,叫做《生命的肖像》。这本书集结了一些病人的照片和他们的临终故事,作者征得了患者的同意,把病人在临终前的照片,以及死后的照片都拍下来,放在一起。通过这本书我感受到,死亡可能并不像我们想象的那么可怕,并不都是血淋淋的、狰狞的。在这本书中,我看到这一张照片,病人去世的表情是非常平静、安详的。到底怎么样能达到这种平静?
思想晚餐
已完成:20%//////////
死亡的“好坏之分”在这个自我解救的学习过程中,我也在观察、思考,我也在想:“死亡”是不是有好坏之分呢?有一句古语,如果恨一个人,就说让他“不得好死”,那么说明有“好死”这回事。如果有“好死”,是不是有它的对立面,就是不好的“死”?其实我们在临床上,经常会看到这样的一些故事。这个故事中的老人家,医院退休的职工,跟我们的关系是非常密切的。他长年患有慢性肺病,最终走到了生命的终点。当血氧饱和度下降,如果不用机器插管和支持,他可能就要将离开人世。但他早早就跟他的老伴说过:“如果我到了那一天,我不能自己喘气的时候,你不要给我插管上机器,我不要遭那个罪。医院工作这么多年,我见多了,我不要这些。”但是当他真的到了那一天,二氧化碳分压很高,氧分压很低,开始呼吸衰竭的时候,医生问:“你们插不插管?”老伴说:“插!我舍不得他。”于是他就被插了管子,这一插就是几年。当他神志清楚的时候,经常想要拔那个管子,所以他的手就被绑起来了。他老伴在接受采访的时候说:“我真的很纠结,我舍不得他。可是我知道,他并不感激我。当他神志清楚的时候,他曾经用口形对我说‘我恨你,我跟你说过不要这些仪器,你就是不听,你看我遭了多少罪。”这种情况,我们医生在临床中天天可以看到。让病人如此痛苦,这是不是我们医疗该做的?是不是最好的?这个值得我们去思考。还有一位女士的故事,她叫洛红。在这儿,我要感谢洛红女士和她的女儿王小迪。之前我也特别请示过她,我说:“我要做一个演讲,可不可以用你妈妈的故事和照片?”她说:“可以!宁大夫,你每次在演讲中提到她,都是对她的纪念。”这位漂亮的女士,她也得了恶性肿瘤,跟肿瘤斗争了四年多,最后走到了生命的终点。她是怎么度过的呢?她的最后时光,是按照她自己意愿度过的。她跟她女儿说:“我想回家,我不想住院”。当时在我们科室,因为气胸她住了一个月的院,之后她出院了,回到自己的家里。但是对于死亡地点,她却说:“我不希望死在家里,医院里走,因为那样有医护人员帮我,不会让你们措手不及。”所以,她的女儿在她最后情况逐渐变差的时候,医院可以收留她,医院。最后的一个月里,医院度过的。哪怕是她住院的期间,也始终按自己的意愿做事。例如,今天两个同事来看她,小张先进来,小张出去以后,小王再进来。她每天尽量自己上厕所,自己做自己的事情。她把自己的衣服、照片都安排好了,这都是洛红女士自己的安排。甚至她在离世前,她跟她女儿说:“你把悼词写好,你先念给我听,我得听听。”她女儿也真的做了这件事情。悼词中有一句:在最后守候和陪伴的这段时光里,我们除了万般不舍,也感到了欣慰与平静。不论是谁离世,家人都会不舍,但是能达到欣慰与平静的,真的是非常少。这就是我们的目标。我们不希望因为一个人的死,让其他所有人活不下去。每个人还是要活下去,但不是痛苦的活,应该是平静的活、幸福的活,我想离世的人也有这种期望吧。我认为,这就是“善终”的样子。思想晚餐
已完成:30%//////////
善终,我们能做什么?那么为了让病人活好,最后再走好,达到“善终”,我们到底应该做些什么呢?我相信这件事很多人都会心里默默地想:该怎么做?有方法吗?有。我们可以做很多事情,为我们自己和家人的“善终”做准备。那么大家为了活好,最后再走好、善终,我们到底应该做些什么呢?这是我们从出生,到长大,到工作,到变老,一直到死亡的过程图。这个配图,是我老公帮我画的。我特别感谢我的老公,感谢他对我事业上的支持。在生命的里程中,我们可能习惯考虑少年、青年、中年,然后在中年后的老年,我们或许很少考虑。现在中国的老龄化特征已经非常明显了,老年人越来越多。你会发现,我们周边的一些亲人,开始走向衰老,甚至走向死亡。那么,我们到底该怎么办?关于这个问题,我认为我们应该积极讨论,而不是采取回避的态度。如果回避,这件事情就会来的很仓促。昨天有一个朋友给我发